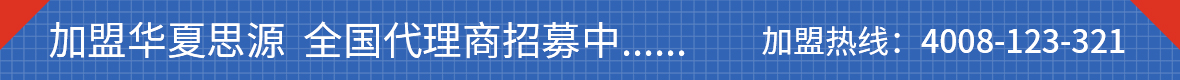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新闻首页>心理培训
爱的研究二上
》》测试:你的心理治疗天赋有多高??《《2拉康对爱的结构化讨论:
2.1爱的形式——转移:
2.1.1转移是爱的研究的条件:
爱的研究之所以必须是精神分析的研究,在于研究的科学性的基础使得精神分析成为唯一可能的出发点。这是因为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是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即研究必须具备直观性,这在科学心理学中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巧妙的实验设计还是质化研究的深度访谈,永远都在其客观位置中处于爱的本质的体验与想象的关系之外。
只有在分析的实践中,在分析家的位置之上,这个科学的基础才能够得到保障,因为只有分析家的位置是处于转移爱的参与者的主体位置同时又不失其客观性。拉康指出,“分析室,同样柔软的,同样所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仅仅是一张爱的床和这个我相信连接到那个东西,尽管在情势的共同目标上所有人们的努力都为了缩减它,加上我们可以给予这个熟悉的字眼的整个共鸣,这不是一个来到此地的情势——就像我一直所说的那样——这是个存在着的最扭曲的情势。允许我们理解它的,正是我们试图抓住的参照、下一次在那个是在社会环境中的爱的情势自身。是在这个尺度中我们能够仔细的靠近、固定弗洛伊德不止一次触及的东西,它是在社会中的爱的位置、不稳固的位置、立即叫它危险的位置、非法的位置,同样是在这个尺度中我们能够评价为什么和如何,在这个所有中最受保护的位置、分析室的位置中,这个爱的位置继续更加悖论的在其中变化的。”[21]
正是分析中的这个转移的尺度使得爱以可定位的方式展现,并且爱在转移中的地位是根本的,拉康说“我们在分析的辞说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谈论爱” [22]。
2.1.2转移提供了爱的基本形式:
爱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基本辞说具有原发性的地位,人们总是用爱来提供解释,而不是用什么来解释爱,至于当弗洛姆指出“爱是一种艺术” [23]时,这同任何对爱的模糊的赞美诗都没有差别,这其中没有任何来自精神分析的根本性的参照。显然,弗洛姆没有理解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发现,“在其(转移)[24]本质中,同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在爱的生活中所呼唤的东西(爱),在转移和这个(爱)之间不存在真正本质上的区别,恰恰仅仅是,转移这个人造现象的结构和我们称作爱、并且更加确切的说是精神层面上的爱-激情的自发现象的结构是等价的。”[25]并且,“精神分析治疗并不制造转移关系,它只是使那种本就存在的转移关系显现而已”[26]例如在杜拉个案中,杜拉对弗洛伊德和杜拉对K先生就展现出了这种等价性,而与他们的关系中所展现的、正是杜拉对父亲的爱恨交织。
因此,“转移爱”即是“爱的转移”[27]。
“爱在分析治疗中是作为转移的一个效果而发生的,贯穿在拉康着作中的一个人为情境如何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的问题使拉康着迷。拉康认为,爱与转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技巧的本质角色在所有爱中的证据。”[28]
在分析中“他(分析家)不可以回答主体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听到的无论多么曲折的呼唤,不然的话他就会看到转移爱形成起来。这个爱除了其人为的产生之外、与爱-激情并无区别。在这时产生它的条件已因其效果而失败,而分析辞说也被化为提出来的在位的沉默。分析家还知道,随着他的回答的缺失,他在主体那里引发出负转移的攻击性甚至仇恨。”[29]
这些在转移中得以展现的爱的现象恰恰揭示出,“那被形容为的性的转移是直到法语中人们称为客体爱的起源的。”[30]例如,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第一篇中讨论了一个男性爱的基本类型,这些男人只爱上妓女一样的女人,并沉浸在对她们的拯救中。在这样的情势中,一个男性是固着在其孩子的位置上,只能在一个像母亲一样被占有的女人身上认出他理想的女人,并在弑父的自居于那个唯一的占有女人的位置、即“拯救”的行动中,完成他对父亲这个真正的男人的认同。[31]这其中展现的不仅是儿时的情感内容和认同形式,而且揭示了爱的现象的宏观结构是转移本身。
拉康说,“转移乃重复……如果转移是重复,那它将总是重复,重复的是挫怅[挫折]。”[32]最初的爱的挫怅是转移的基本动力,在这个动力所导致的无止境的重复的爱的现象中,我们可以说:爱是转移。这是爱的现象的基本形式。
2.1.3爱-恨-无知:
“要记住,弗洛伊德在谈及人们归之于转移的情感时坚持要在其中分辨出一个现实的因素来。他的结论是,如果想要使主体相信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情感都不过是神经症的简单的转移的重复,那么这是在模糊主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这些情感表现为是初始的,而我们自身的魅力总是一个随机的因素,这儿看来就有了一个谜。
但是,如果将这个谜置于主体的现象域来观察,而主体又是构成于其对真理的寻找,那么就可解开这个谜了。这只是要求助于历史的成果,佛教提供了这些成果(他们并且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以便使人可在这个转移的形式中看到生存的错误。佛教徒们指出了三种:爱、恨和无知。在人们原先称之为正转移的活动中,我们将这些成果的同等物理解为分析行动的反效果,在这个存在的方面,每一种都能为其他两种所阐明,即使第三种常常因其与主体的接近而被遗忘而不为人接受。”[33]
这个“爱-恨-无知的三段式”[34]是拉康对佛教三毒“贪、嗔(也作瞋、瞠)、痴”的翻译,通过这个翻译,拉康将其思想同汉传佛教对爱的理解联系在一起。拉康在《转移》讨论班中说,“《会饮篇》”是“爱的结构的主体”[35],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苏格拉底说爱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36]。通过这样的有些隐晦的滑动,拉康在其对爱的形式化阐述之外确立了爱的基本含义,这和弗洛伊德对爱的基本讨论是相合的,在《冲动及其变迁》中,弗洛伊德讨论了爱的运作,他说:“如果后来一个客体发展成为快乐的一个源泉,它就会被爱”[37]。有所不同的是,拉康借助佛教的教诲所阐释的这个三段式与佛教的立场是对立的,在佛教中,三毒是最大的觉悟的障碍,是修道之路的第一道大坎,例如《华严经》中的一首谒所表达的:“当愿众生,弃贪嗔痴,蠲除罪法。”[38]相反,拉康说,这个三段式是“存在的激情”[39]。
“(存在)这样形成:在符号与想象连接处的激情或渊(裂口),如果你想的话,或者被称作爱的刀刃线;在想象与实在连接处的这被称作恨的;和在实在与符号的接口处这被称作无知的。”[40]结合拉康后期的三界图式:
可以发现爱-恨-无知居于的三界的交界之处,它正构成了一个精神结构的三界运转的动力源。在这里,拉康对爱的定义是一个理想的定义,即“升华的爱”[42],处于想象和符号交接的产生并确立意义的领域,它的客体是“存在中的存在”[43]。但是拉康并不总是在这个理想的意义上谈爱,那个在想象界中的、更加具有广延性和一般意义的爱也同样是拉康经常讨论的主题。
2.1.3.1自恋与作为基础的镜子阶段:
“爱是自若的,并具有一个基础性的自恋结构,因为‘一个人在爱中所爱的正是他自己的自我,某人自己的自我在想象的水平上得以实现’”[44]。自恋是爱的现象的精神结构基础,弗洛伊德发现,客体爱是以自恋为前提的,但弗洛伊德对于自恋力比多的论述缺乏其运动轨迹的空间基础,拉康在镜子阶段的发现中解决了这个自恋的根本问题,将自恋的结构性基础更加明析的确立了下来,镜子阶段的理论蕴含了自恋的所有真理:
1“主体借以超越其能力的成熟度的幻象中的躯体的完整形式是以格式塔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得的。……这个格式塔通过它体现出来时的两个特征,象征了‘我’(自我)在思想上的永恒性,同时也预示了它异化的结局。”[45]孩子在镜中获得的是一个整体的格式塔形象,这个形象具有关键的成形作用,在面对自身镜像时,孩子身处于“认同过程”中,通过这个根本的认同“‘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46]。在镜中的虚像是理想自我,自我在这个镜像认同的过程中以一个根本的虚像的方式生成了。镜子阶段是人类个体成长过程中精神特征的第一次正式登场,在镜像的格式塔介入的过程中,想象的优先性被确立了,这也是拉康所说的“想象的奴役之结”[47]。
在这个认同于外在的自身虚像的过程中,自若的孩子的爱若性得以转移到外部,这使得孩子与镜像的关系成为爱若的和“本质的力比多关系”[48]。由于镜像认同是一个对外在、异化的象的认同,它也就由此为享乐由自身的躯体排除奠基,这使得后来男人只有在女人的享乐中才能获得享乐成为可能,正是自若在镜子阶段中的自恋中得以转移才产生了后来的“享乐的隐喻”[49]。
对外在的象的认同的另一个效果是引入了客体。“这里的那客体,在这个水平上(自恋、想象),被引入了,因此为了主体固有的象、客体永无休止地与拥有主体的爱互换。自我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引入,因此,从这第一个关节起,也就是从《论自恋:导论》开始,是围绕着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自我的幻象和一个理想的形式化,它自己抓住其领域、变得更好,至少来到主体的内部对某物给出一个形式,从此他将屈从在这东西上,因此认同的问题连接到这个二重心理学,将从此使主体处于这个依赖中,通过与这个他自己的理想化的、强迫的象的关系,弗洛伊德后来总是给予如此崇高地位的关系,是在这个关系中、在这个幻象的关系中客体的概念被引入。”[50]
2镜子阶段同时还以两种方式确立了人的本质的攻击性。
其一,人类是早产儿,镜子阶段的孩子是通过外在的格式塔形象整合了并不协调的碎片化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不协调与完整形象的冲突始终存在,例如乔丹这样的球星仍然会投不进球。这就使得自我与自身之间始终存在一条裂口、一道渊,它形成了紧随理想形象之后的无处不在的攻击性张力。
其二,镜子所映出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虚的空间,自我的虚像就投射在这里,也就是说,想象的自恋空间始终大于现实的空间,这是自恋直接的攻击性本质。这个攻击性是“特别与空间的范围有关的人的自我的意愿坐标”[51],“正是这个空间领域在镜子中映射到别人的领域中去的主观可能性给予了人类空间的原始‘几何’结构”[52]。
3镜子阶段之所以是镜子阶段而不是镜像阶段,在于镜子本身具有至关重要的的作用。“镜子或许有时会暗示自恋的机制,特别是随后我们将遭遇到的破坏或攻击性的维度。但是,它也起着另一种作用,一种作为界限的作用。它是不能被穿过的那个东西,并且它参与的唯一组织便是客体[对象]的不可能接近的那种。”[53]也就是说,镜子是一堵墙,同时在镜子铆定了目光,也就是说,客体小a在此能够以一个并非逃离的而是无比确定的方式存在,构成主体与其镜像之间的固定的动力源,因此,镜子是(a)mur,即“渊墙”,这堵渊墙本身虽然不是是爱、amour,但是它给予了爱的维度。
如图所示,当一个主体处于其自我与彼者的想象的诱惑关系时,这个彼者的躯体就是一面镜子,并且仅仅是镜子,主体是在那里看到了它通过彼者躯体的这面镜子所投射的自我的虚像的理想自我,因此,小彼者的地点拉康用了“a’”来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拉康说想象的关系是一个“奴役之结”。
拉康在提出了客体小a的概念之后,并没有回过头来以客体小a的理论体系重新阐释“L图”,而恰恰,如果将拉康的客体小a概念引回到L图,就会确立一个根基更加夯实的精神系统的运转结构。居飞在其《科学、精神分析和客体小a》中完成了这个重构。
通过对哥德尔定理的引入,居飞证明了“‘010-101’就是这个系统本身的不可判定命题。……不可判定的命题就类似于一个客体小a一样,由象征界构造,可以被想象,但总是有剩余。因此通过对有拉康系统得到的函数系统的研究,图4‘010-101’轴恰当的表达了拉康的客体小a的概念。”[56]在此基础上再回到L图,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动力结构:
通过客体小a的核心的引入,L图才能够稳定下来并且进入运转,只有在如图5这样的客体小a引入的五行结构中,拉康的网络运转模型才能得以实现。镜子阶段的那面镜子就居于这个五行的中心。
4镜子阶段作为想象的诱惑的基础也同时隐含着符号的根本因素。
其一,“符号秩序存在于携带和抱持婴儿的成人身形之中。在主体欢喜的将他的形象假定为他自己之后的时刻,他转过他的头望向这个成人——这个成人代表了大彼者——好像请求成人对这个形象的认可。”[57]孩子对自身形象的确认是需要母亲的话语的,母亲的一句“这是你自己”的符号介入在孩子的想象认同中起着铆定的作用,这也是想象的奴役之结能够得以打破的最初基础。
其二,这个认同的时刻所带来的是“‘你既如此’……的狂喜”[58],“因为它导致了主人性的一个想象的认识:‘(孩子的)快乐是由于他的想象的胜利,即他预期了一个实际上他还未获得的肌肉协调性的程度’”。[59]这个狂喜的时刻不禁使我们自问,这个符号的确认是否包含形象本身的符号?多尔多发现,形象的诱惑中脸是一个区分性的因素,认知心理学的实验也揭示婴儿对脸有区分性反应,也就是说,脸是躯体的符号。
当拉康说“躯体意象作为能指”[60]时,他只是把这个内化的形象作为了能指,而没有推论普遍的形象能指系统。霍大同先生提出“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指出存在“视觉的能指”[61],并且这是一个能指的系统,像汉字的形符那样发挥这普遍性的能指效用,这展现在视觉平面的抽象机制所结构化的几何学中以及毕加索以来的现代绘画中,也出现在我们每天面对的一切形象中。同时,由于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那么想象界与实在界就是如同汉字的形与义那样的“相似关系,亦即隐喻的关系”[62],这再次确认了想象诱惑的基础以及其优先性,而符号界和想象界以及符号界和实在界之间则是“空间临近的关系,亦即换喻的关系”[63]。
正是形象能指的存在使得人类个体总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陷入到想象的诱惑中,同时,正是形象能指的存在使得一个个体在对其所爱之人仅仅视觉的发现中进入到镜子阶段式的“我既如此!”的狂喜中。
2.1.3.2爱情的基本形式——爱-恨-无知中的迷恋:
“Liebe(爱),弗洛伊德说事实上就是人们能够称作‘正常的’爱的东西,但是这全是为了增加、一旦这假设的正常完全不符合其他的就仅仅符合在阿里斯多潘的神话的诗化传说中的信仰,这分成两半的人类存在,男人和女人,不顾一切的力图重新找回他们失去的统一。但是普通的爱,它在总有一天我们燃烧了所有的火焰上,我们这些好神经症者们,这是:Verliebtheit(迷恋)……并且这干脆是更不田园的。”[64]
在西方,具有神话之维的“爱”和生活中的爱情并不直接等同,但由于没有中文在这方面的区分性,爱往往蕴含了太多的混淆,弗洛伊德、拉康都敏锐的注意到了这同一个能指中蕴含着的混淆,对于生活中确切的爱情的维度,弗洛伊德将其区分为“迷恋”,拉康将其充分的落实在爱-恨-无知的三段式中。
拉康说,“发生着这些事,正是在这个偶然成熟的力比多的相遇中,并且由于在爱若——为了应用最后一个弗洛伊德的词汇——的平面上,对自恋的象的关系在迷恋的平面上通过,就是在这个时刻,自恋的象,作为诱惑和想象平面上的使疯狂,变成了确切地说是这个特殊的关系的投注的象,这个特殊的关系是迷恋,是我们认识的爱界的最明显的现象学地东西。
这样解释这些东西,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成熟过程连接在发育中,连接在另一个东西的一种充满、甚至溢出所决定的主体的生命演变中,这个东西直到那时都被包含在未成熟主体的力比多的原初开口的空中。这个我们称作性成熟前力比多的东西在那个时刻是一个感觉敏感的点,在这个点上人类闪动在他的虚弱,即他的自然虚弱点和某种自然实现之间。就是那儿,幻象的点在爱若与死冲动、爱与恨间闪动。更简单的是,我相信这是表达、达到理解、领会的最简单的方式,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自我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弗洛伊德似乎是最难于回答的,你们可以自己参见他的着作《自我与它我》,在自我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自己扮演在回复的可能性、爱中恨恨中爱的瞬间转变中,外号是自我的去性化力比多所扮演的那个角色。”[65]
爱与恨的这个对子是精神分析的出发点之一,弗洛伊德总结其临床观察,在《冲动及其变迁》中提出,“冲动内容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只在一种情形下被观察到了——爱向恨的转化。”[66]这一个观点,是弗洛伊德1924年以后确立的,在之前的版本中,弗洛伊德说的是“爱与恨之间的转化”,拉康的工作证明弗洛伊德最初的领悟才是对的;同时,弗洛伊德还说,“作为一种对客体的关系,恨要比爱古老”[67],这也是将被拉康进一步阐释的。故此,拉康说,“爱在其与恨的矛盾的原初的联结中,应是一个嵌入了自身的项。”[68]
在这个对子中,迷恋与爱的关系是拉康所区分的重点。
- 凡本网注明"来源:华夏思源心理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华夏思源心理网,转载请必须注明华夏思源心理网,http://cms.siyuanren.com违反者本网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 本网转载并注明自其它来源的作品,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及时联系本网站进行删除。